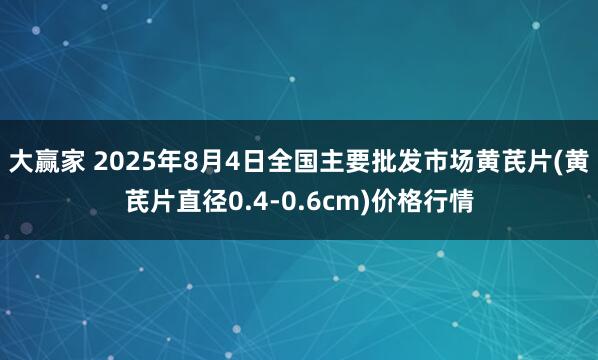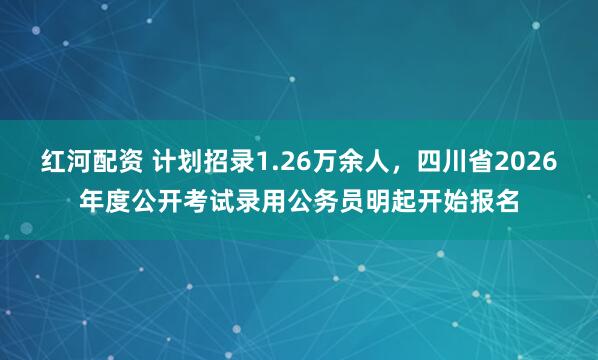港股T+0配资 炎症——站在心肾共病的交叉路口:从机制到治疗的新启示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港股T+0配资
心血管疾病(CVD)与慢性肾脏病(CKD)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患者死亡的两大主要慢性疾病[1-3]。二者常合并存在,在增加彼此发生率的同时,二者的共存也与更严重的不良预后相关[4]。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SCVD)与CKD存在较多共同的风险因素,如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T2D),此外,ASCVD与CKD间存在密切的病理生理交互机制[5-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慢性低度炎症作为二者的共同病生理基础之一,被视为连接ASCVD与CKD的“共同土壤”[6-10]。在此背景下,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类药物因其在改善代谢的同时展现出的抗炎作用引起了一定关注[11]。
本文从炎症在ASCVD/CKD中的作用机制出发,解读最新相关研究结果,并探讨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GLP-1RA在上述人群中降低炎症水平的潜在价值。
炎症:连接ASCVD与CKD的共同病理基础
自1999年Russel Ross教授提出动脉粥样硬化(AS)的“炎症学说”以来[12],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炎症是动脉粥样硬化及其并发症的关键驱动因素。动脉粥样硬化起始于血管内皮的损伤和功能障碍[13,14],脂蛋白的浸润、滞留与氧化修饰导致内皮损伤,触发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应答[15],募集的免疫细胞通过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加速泡沫细胞形成、诱发斑块内出血、分泌基质降解酶从而促进AS病变进展及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生[15]。因此炎症反应在ASCVD的发生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6],贯穿AS斑块的形成、发展直至不稳定甚至破裂[16]。

图1.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各阶段及参与AS斑块不稳定性-破裂的炎症标志物[15]
LDL:;VSMC:血管平滑肌细胞;ECM:细胞外基质;IL-1:白细胞介素-1;IL-6:白细胞介素-6;IL-18:白细胞介素-18;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MCP-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G-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IL-1R:白细胞介素-1受体;IRF-1:干扰素调节因子–1;ICAM-1:细胞间黏附分子-1;V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ox-LDL:氧化低密度脂蛋白;LP-PLA2: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MCP-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CRP:C反应蛋白;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
炎症在CKD的进展中同样也扮演重要角色[10]。CKD患者体内毒素潴留、氧化应激、微炎症介质产生增多等因素导致该人群患者存在慢性低度炎症状态[17],而炎症进一步与氧化应激形成正反馈循环,进一步彼此加剧[18]。最终,慢性炎症驱动的肾脏纤维化使功能性肾单位进行性丧失,肾功能不断恶化[19]。此外,CKD患者的病理表现之一蛋白尿亦可作为一种致炎因素,激活肾小管上皮细胞产生炎症因子,从而加速肾损伤[20]。整体上,慢性炎症通过肾组织纤维化、肾小管损伤等途径参与了CKD的发生及进展[19,21,22]。

图2.导致肾脏纤维化与肾小球损伤的不同肾细胞类型中的炎症通路[23]
a.在足细胞中,葡萄糖和同型半胱氨酸可诱导ROS的产生,促使TXNIP与NLRP3结合,从而激活NLRP3炎症小体,导致足细胞凋亡、足突融合(足突消失)和蛋白尿。b.单核细胞在FA或晶体(如草酸盐或尿酸晶体)刺激下可表达pro-IL-1α,后者可被钙蛋白酶切割。此外,pro-IL-1α在单核细胞表面的表达可通过IL-1R1介导单核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诱导内皮细胞表达VCAM-1,从而进一步促进单核细胞-内皮细胞黏附。c.白蛋白通过megalin和cubilin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进入肾小管上皮细胞后,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并释放线粒体ROS。这一过程激活NLRP3炎症小体,介导SMAD3依赖性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和TGF-β的产生,诱导上皮-间充质转化(EMT)和肾脏纤维化。d.巨噬细胞吞噬受损的肾小管上皮细胞(TECs)释放的DNA,激活Aim2炎症小体,进而通过GSDMD介导的膜孔形成和细胞因子释放,引发炎症反应。e.IL-1β通过MYC介导的信号通路抑制基质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氧化磷酸化,促进糖酵解过程,这一过程与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与TLRs的相互作用共同作用,诱导αSMA和胶原蛋白的释放,从而促进成肌纤维细胞转化和纤维化。ROS:活性氧;NADPH: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TXNIP:硫氧还蛋白相互作用蛋白;NLRP3:NLR家族含吡喃结构域蛋白3;FA:脂肪酸;pro-IL-1α:前白介素-1α;IL-1R1:白细胞介素-1受体1;VCAM-1: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megalin:巨蛋白;cubilin:库比林蛋白;SMAD3:母源抗骨形态发生蛋白信号转导蛋白同源物3;TGF-β:转化生长因子-β;DNA:脱氧核糖核酸;Aim2:黑色素瘤缺失因子2;GSDMD:消皮素 D;IL-1β:白细胞介素-1β;MYC:髓细胞增生癌基因;TLRs:Toll样受体;αSMA:α-平滑肌肌动蛋白;IRAK4:白细胞介素-1受体相关激酶4;Nterm:N末端;p62:核孔蛋白62。
CKD作为ASCVD的风险因素之一,其引发的慢性炎症不仅是肾脏疾病进展的关键环节,也是促进CKD患者疾病发生和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CKD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体内多种炎症介质[如白细胞介素-6(IL-6)、hs-CPR(高敏C反应蛋白)等]清除减少[24],同时尿毒症状态还可直接激活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导致系统性炎症水平升高[25]。这种慢性全身炎症会作用于心血管系统,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26]。另一方面,ASCVD患者的慢性炎症同样会对肾脏造成不良影响,炎症介质可经血液循环到达肾脏,引起肾脏损伤[27],形成心肾之间的恶性循环。
因此,ASCVD和CKD通过慢性炎症这一共同通路相互影响:CKD的炎症状态加速ASCVD发展,而ASCVD的炎症反应促进肾功能恶化,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加剧,上述炎症介导的心肾交互作用,解释了ASCVD患者合并CKD时患者预后的恶化。
炎症标志物新证据:CRP水平与ASCVD患者肾脏预后不佳相关
C反应蛋白(CRP)是肝脏在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炎症细胞因子刺激下产生的急性期蛋白,已成为临床上评估系统性炎症水平的可靠标志物[28,29]。hs-CRP是一种高灵敏度定量检测CRP的生物化学检验方法,该检测采用改良的高灵敏度测定技术,可精准测量血浆中极低浓度的CRP水平[30]。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关注了CRP/hsCRP在预测CKD进展和肾脏预后中的价值。
2025年6月发表在《美国肾脏病杂志》的一项大规模队列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揭示了在ASCVD患者中,系统性炎症水平与不良肾脏结局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4]。
研究共纳入83,928名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的ASCVD患者港股T+0配资,通过CRP水平评估基线炎症状态,并中位随访6.4年观察肾脏结局,旨在探讨系统性炎症(以CRP为标志)与ASCVD成人患者不良肾脏结局之间的关联[4]。
研究发现,相较于CRP<1mg/L的患者,更高的CRP水平与复合肾脏结局(定义为eGFR持续下降超过30%或肾衰竭)以及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率显著相关[4]。具体而言,与CRP<1mg/L者相比,CRP升高组(>3-10mg/L和>10-20mg/L)发生复合肾脏事件的风险分别增加24%和35%,AKI风险分别增加34%和37%。CRP每升高1个标准差(SD),不良肾脏结局风险增加7%[4]。整体而言,CRP水平越高,ASCVD患者发生肾功能恶化和AKI的风险越大,预后越差。

图3.不同CRP水平人群复合肾脏结局及AKI风险

*校正了年龄、性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生时间、估算肾小球滤过率、白蛋白尿、合并症(糖尿病、高血压、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癌症、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外周动脉疾病、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房颤和风湿性疾病)、所进行的手术操作(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以及正在使用的药物(抗血小板药物、非甾体抗炎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利尿剂、钙通道阻滞剂、地高辛、降脂治疗[他汀类药物、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kexin 9型抑制剂、依折麦布])。
该研究结果提示:在ASCVD患者中,高水平的CRP与不良肾脏结局风险增加相关。
司美格鲁肽:超越降糖——从降糖药物到心肾保护中的抗炎
鉴于慢性炎症在ASCVD和CKD中的核心作用,针对炎症的干预策略有望同时改善心肾结局。在现有治疗手段中,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司美格鲁肽已通过SUSTAIN 6研究证实可以降低T2D合并CVD或CVD高风险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3P-MACE: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梗或非致死性卒中的复合终点)发生风险达26%;首个GLP-1RA的肾脏结局试验FLOW研究证实司美格鲁肽可显著降低CKD伴T2D患者的主要肾脏事件复合终点(eGFR持续降低≥50%、持续性eGFR<15ml/min/1.73m2、起始长期肾脏替代治疗、因肾脏疾病或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达24%。同时,随着对于司美格鲁肽心肾获益的探索愈加深入,近年研究结果提示司美格鲁肽也存在一定的抗炎作用[11]。
机制角度:分子水平上,司美格鲁肽可抑制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炎症小体激活,减少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IL-18)产生[31,32];细胞水平上,司美格鲁肽通过降低中性粒细胞中C-X-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2(Cxcl2)、S100钙结合蛋白A8(S100a8)和S100钙结合蛋白A9(S100a9)的表达,可能有助于减轻心脏炎症和氧化应激[33];在组织层面,司美格鲁肽可减轻血管内皮炎症和肾脏局部炎症反应及纤维化[34]。
多项随机对照试验(RCT)结果探讨了司美格鲁肽在2型糖尿病和/或超重/肥胖患者中对炎症标志物hsCRP的影响,结果均提示司美格鲁肽可在上述人群中降低hsCRP水平。

SUSTAIN 2研究共纳入1231例二甲双胍、噻唑烷二酮类或两者联合治疗失败后2型糖尿病患者,基线时hsCRP 2.33mg/L。司美格鲁肽1.0mg的受试者在治疗结束时(第56周),hsCRP水平较基线降低1.3mg/L(P<0.05)[35,36]。
PIONEER 2研究共纳入822例二甲双胍控制不佳的2型糖尿病患者,基线时hsCRP 2.7mg/L,治疗结束时(第52周),司美格鲁肽片组的受试者hsCRP水平较基线降低37%(P<0.05)[37]。
STEP 3研究共纳入611例不合并糖尿病的超重/肥胖患者,基线平均hsCRP 4.52mg/L。第68周时,司美格鲁肽2.4mg组的受试者hsCRP水平变化为-59.6%(P<0.001)[38]。

除降低hsCRP外,部分研究表明,司美格鲁肽可降低其他促炎因子水平,如TNF-α及其受体、IL-6等[39]。
上述研究结果均提示司美格鲁肽的抗炎作用可能是其心肾保护作用的潜在机制之一。2024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指南建议在CKD合并糖尿病患者中优先考虑GLP-1RA,2025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指南也已将GLP-1RA推荐为ASCVD或高风险患者的一线选择[40,41]。
结语
随着对炎症在ASCVD和CKD中作用机制认识的加深,抗炎治疗策略的探索为改善患者预后提供了新的视角。司美格鲁肽在ASCVD和CKD共病管理中从炎症视角体现了其独特价值。未来仍需更多研究来进一步阐明司美格鲁肽的抗炎机制港股T+0配资,以期在现有治疗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相应患者的管理。
专家简介

郭远林 教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主任医师、心血管代谢中心副主任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心血管代谢医学专委会,常务委员
中国心胸心血管麻醉学会基层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CDQI国家标准化心血管与代谢疾病中心,秘书长
亚洲心脏学会(AHS)心血管预防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代谢性心血管疾病学组,委员
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心血管代谢医学专委会,常务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常务委员&银屑病共病学组副组长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老年医学专委会,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第三届心脏与血管专委会,委员
参考文献:
[1]Yadav R, et al. Med Sci (Basel). 2025; 13(2): 80.[2]Jiayi H, et al. Pharmacol Res. 2024; 202107139.[3]Saeed Z, et al. Int J Mol Sci. 2024; 25(16): 8705.[4]Mazhar F, et al. Am J Kidney Dis. 2025; S0272-6386(0225)00875-00873.[5]Vallianou N G, et al. Curr Cardiol Rev. 2019; 15(1): 55-63.[6]Olsen M B, et al. JACC Basic Transl Sci. 2022; 7(1): 84-98.[7]Carracedo J, et al. Front Cell Dev Biol. 2020; 8185.[8]Wang T, et al. Diabetes Metab Syndr. 2019; 13(1): 612-615.[9]Li Y, et al. BMC Public Health. 2025; 25(1): 1685.[10]Kadatane S P, et al. Cells. 2023; 12(12): 1581.[11]Paschou I A, et al. 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 2025.[12]R R.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9; 340(2): 115-126.[13]Wolf D, et al. Circ Res. 2019; 124(2): 315-327.[14]Frak W, et al. Biomedicines. 2022; 10(8).[15]Attiq A, et al. Eur J Pharmacol. 2024; 966176338.[16]Henein M Y, et al. Int J Mol Sci. 2022; 23(21): 12906.[17]Frak W, et al. Antioxidants (Basel). 2024; 13(6).[18]Stenvinkel P, et al. Kidney Int Rep. 2021; 6(7): 1775-1787.[19]Roccatello D, et al. Autoimmun Rev. 2024; 23(4): 103466.[20]Makhammajanov Z, et al.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24; 39(4): 589-599.[21]Liu B C, et al. Kidney Int. 2018; 93(3): 568-579.[22]Morinaga J, et al. Kidney Int. 2016; 89(2): 327-341.[23]Speer T, et al. 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 2022; 18(12): 762-778.[24]Yilmaz M I, et al. Clin Nephrol. 2007; 68(1): 1-9.[25]Martos-Rus C, et al. Sci Rep. 2021; 11(1): 2974.[26]Arida A, et al. Int J Mol Sci. 2018; 19(7).[27]Rosner M H, et al. Semin Nephrol. 2012; 32(1): 70-78.[28]Plebani M. Clin Chem Lab Med. 2023; 61(9): 1540-1545.[29]Amezcua-Castillo E, et al. Biomedicines. 2023; 11(9): 2444.[30]Banait T, et al. Cureus. 2022; 14(10): e30225.[31]Wang L, et al. Int J Mol Med. 2021; 48(6): 219.[32]Kelley N, et al. Int J Mol Sci. 2019; 20(13): 3328.[33]Pan X, et al. Mol Cell Biochem. 2024; 479(5): 1133-1147.[34]Tian S, et al. Adv Sci (Weinh). 2025; 12(4): e2409781.[35]Aroda V R, et 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7; 5(5): 355-366.[36]Ahren B, et 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7; 5(5): 341-354.[37]Rodbard H W, et al. Diabetes Care. 2019; 42(12): 2272-2281.[38]Wadden T A, et al. JAMA. 2021; 325(14): 1403-1413.[39]Tiba A T, et al. J Med Life. 2023; 16(2): 317-324.[40]Hood M M, et al. J Behav Med. 2016; 39(6): 1092-1103.[41]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C. Diabetes Care. 2025; 48(1 Suppl 1): S181-S206.
“此文仅用于向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提供科学信息,不代表平台立场”

医学界心血管领域交流群正式开放!
加入我们吧!

顺阳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